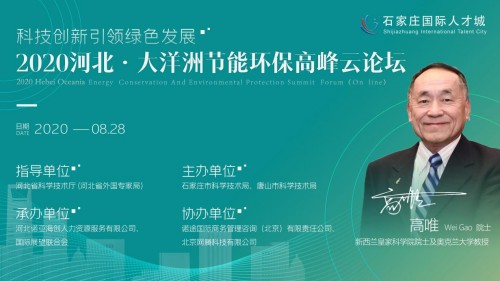“轻体力劳动”走红:年轻人重新定义“好工作”
作者:袁叶雨萌
夜晚十点半,博士生贺辰结束了一天的科研工作。他戴上头盔,点开接单界面,开始了他的外卖骑手工作。在晚风中飞驰,迟迟没有进度的科研任务被抛在脑后。
“送外卖成为一种独特的脑力休息方式。”贺辰说,他并不需要过多考虑,还能在出汗的同时赚一些零花钱。
像贺辰这样投身轻体力劳动的年轻人正越来越多。豆瓣小组“轻体力活探索联盟”创建于2022年11月,已聚集了超过10万名“探索者”。
他们原先大多从事脑力劳动,在小组里分享从办公室“逃”向轻体力活的经历:前媒体人分享咖啡拉花的技巧,离职不久的大厂员工记录下应聘服务员带来的幸福感。
现象观察:从脑力倦怠到体力复苏
“去年8月,我的体检单数据很不好。在公司的这几年,体重已增加了接近60斤。”广州互联网大厂员工张佳瑞看着不尽人意的健康状况,终于下定决心提交了离职申请,走进了“兰州拉面培训班”。
在25天的拉面课程中,张佳瑞瘦了接近20斤。之前看电脑导致的颈椎病和脖子前倾有了改善,身心状态都在拉面的揉捏摔打中好了许多。
在福建宁德的工厂里,20岁的郑娴正在从事燃料质检工作。学习旅游管理专业的她,做过酒店前台、移动营业员、水利局文员,最终选择进厂。
“现在的工作除了必要沟通,不用额外交流。”郑娴说,自己干活勤快,老板认可,绩效分高,对现在的工作也很有归属感。
价值重构:从“悬空”到“具体”的劳动体验
武汉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副教授陈武指出,办公室久坐、长期脑力劳动,易导致身心失衡,轻体力活能通过身体活动弥补精神疲劳,可视为是一种维持身心健康的有效方式。
在传统职业认知框架中,“坐办公室”与“体面”“精英”深度绑定,“体力劳动”则常被贴上“低价值”“重复性”的标签。然而,这代年轻人正在用行动打破这一固有观念。
张佳瑞认为,轻体力活的成果“独一无二”。她在帖子中写道:“建议从大厂离职的人员都来试试纯体力活,踏实做事真的能提升生活幸福感。”在她看来,这种体力活能带来直接、即时、正向的反馈。
对于陷入职业倦怠的年轻人而言,轻体力活带来的是更有“确定性”的奖励。一位从程序员转行做家居维修的受访者表示:“修好一个漏水的水龙头,客户会真诚地说‘谢谢’;组装完一套家具,孩子会在新床上开心地打滚。这些具体的反馈让我觉得,我的工作真的在改变别人的生活。”
现实挑战:轻体力活并不“轻”
然而,轻体力活的体验一点也不“轻”。
花艺是该小组中最常被提及的职业之一,但尝试过的桔年说:“我只能做分装,一看插花就知道自己做不了。”桔年也考察过咖啡师这一职业,咖啡师虽然入行门槛比较低,但工作强度也远超出她的承受范围。
张佳瑞坦言,就算自己是拉面培训班中“最偷懒的人”,一天的课程后仍然“体力透支、手臂肩膀都酸痛”。
尝试将外卖工作作为兼职后,贺辰也很快发现,对他而言全职送外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职业选择,“一旦把送外卖作为正式工作,那么原先时间自由又可以适当运动的优点就不存在了”。
陈武提醒,要理性判断和选择,每种职业都有门槛和难度,轻体力活的挑战程度并不亚于办公室工作。
深层思考:职业价值观的多元化转向
津云谈到周围人对轻体力活的看法:“有的人并不认可这个工作的价值。不是所有人转型后都能自洽、坚持下去。很多人只是想转换生活方式,觉得新鲜才尝试,可能一两个月后就回到了原行业。”
脑力倦怠的大厂人对体力活抱有一种浪漫化的向往,张佳瑞把这种现象描述成“围城”。在张佳瑞的分享裸辞学拉面的帖子底下,有一条评论:“你们只是因为有学历,有托底,短暂体验一下就说可以解决职业倦怠,但是你们还有机会回到大厂。”
张佳瑞对此表示赞同:“的确,有退路的人,和靠体力劳动吃饭的人,对体力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”
对郑娴来说,工厂工作是当下最好的选择:“现在的工作薪资待遇和我自己对工作的满意程度,都比以前的工作好很多。”
陈武支持年轻人多体验不同类型工作,“体验越多,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”,多尝试能帮助建立全面认知,避免被单一职业类型局限。
贺辰说,或许博士毕业后,自己就不会再送外卖了。“能靠劳动赚钱的职业都是好工作,何况能选择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的时候,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幸福。”
从逃离脑力倦怠到寻求具体劳动,从追求外在认可到注重内在价值,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职业选择,重新定义什么是“好工作”。在这场静默的职业革命中,“轻体力劳动”不再仅仅是谋生手段,更成为了一种探寻自我价值的生活方式。